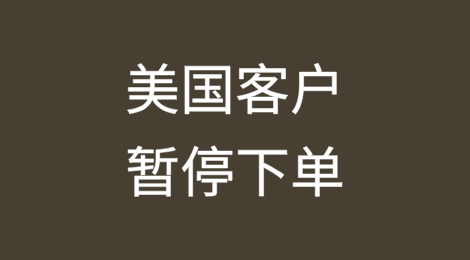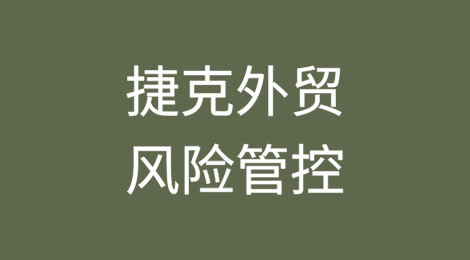实施反外国制裁法规定要点解读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规定》”)于近日出台。该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制裁法》”)于2021年生效以来,我国进一步充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工具箱”的重要举措。《规定》旨在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本文试简析《规定》要点。仓促成文,难免疏漏。虽笔力未逮,然愿以拙见引玉,与诸君共探其奥[1]。
1
明确反制措施的适用范围
(《规定》第3条)
对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干涉我国内政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歧视性限制措施”),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虽然《规定》第3条对 “歧视性限制措施”进行了诸多限定,但笔者认为“歧视性限制措施”最核心的特征为“以干涉我国内政为目的”,主要包括外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所谓“单边制裁”。如某些国家和组织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等议题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相较而言,对于他国制定的旨在维护其经贸、科技领域竞争优势的制裁措施,或旨在干涉除我国外第三国内政的制裁措施,则并非《规定》第3条及《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所称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对反制措施适用范围的限制,体现了精准制裁的立法态度。
对外国国家、组织、个人实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危害行为”),我国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危害行为”包括外国反华势力、敌对势力进行的相关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如某些实体和个人鼓吹、煽动、资助台独、疆独、藏独、港独等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在《反外国制裁法》第15条中,对于“危害行为”,只有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前提下,才应参照执行《反外国制裁法》。此次《规定》的出台,明确了《反外国制裁法》直接适用于“危害行为”,厘清了反制措施的适用范围。
2
明确可被列入反制清单的主体
(《规定》第3条)
结合《反外国制裁法》第4和第5条,《规定》第3条中国务院有关部门针对“歧视性限制措施”及“危害行为”有权将“有关组织、个人及与其相关的组织、个人”列入反制清单、采取反制措施。具体包括如下主体:
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
实施、协助、支持“危害行为”的外国国家、组织、个人;
与上述1、2项中所列主体“相关的组织、个人”:
-
在上述组织被列入反制清单的前提下,包括其高级管理人员,其实际控制人,其实际控制、参与设立/运营的其他组织;
-
在上述个人被列入反制清单的前提下:包括其配偶,直系亲属,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
(以上1-3项,合称为“受制裁主体”)
3
明确反制措施的实施机关,细化反制措施
的内容(《规定》第6-9条)
《规定》在《反外国制裁法》第6条的基础上,明确了反制措施的实施机关,对反制措施予以细化,具体包括:
国务院外交、国家移民管理等有关部门有权对受制裁主体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
国务院公安、财政、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海关、市场监督管理、金融管理、知识产权等有关部门,不仅可对受制裁主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亦可对我国境内的现金、票据、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基金份额、股权、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财产和财产权利进行查封、扣押、冻结。
《规定》第7条将反制措施的辐射范围由财产扩展至财产性权利,显著增强了反制措施的可执行性。在实务中,受制裁主体在中国境内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正常商业运营可能因其现金、知识产权等被采取强制措施而遭受负面影响。需注意的是,该条仅适用于我国境内的财产和财产权利,不构成“长臂管辖”。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禁止或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受制裁主体进行教育、科技、法律服务、环保、经贸、文化、旅游、卫生、体育领域的交易、合作等活动。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禁止或限制受制裁主体从事以下活动:
-
禁止或者限制其从事与我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
禁止或者限制其在我国境内投资;
-
禁止向其出口相关物项;
-
禁止或者限制向其提供数据、个人信息;
-
取消或者限制其相关人员在我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或者居留资格;
-
处以罚款。
《规定》第7-9条拓展了反制措施的外延,受制裁主体将在科技、经贸、数据等核心领域遭受限制,不仅无法在华开展新业务,既有业务亦可能被“禁止或限制”。受到制裁的外国公司及其境内主体可能因交易终止、原材料进出口受限等原因触发供应链上下游的连锁违约事件,遭受严重经济损失。
《规定》的施行将督促外方重新评估“歧视性限制措施”、“危害行为”对其商业活动的潜在影响,推动其在对华交往中谨慎行事。
4
反制措施的动态调整及受制裁主体
的救济途径(《规定》第14、15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依职权或依申请调整反制措施。
决定采取反制措施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会结合反制措施在执行中的情况和具体效果,通过暂停、变更或者取消的方式对反制措施进行动态调整。
受制裁主体通过实施改正行为、消除行为后果等方式,可申请暂停、变更或者取消对其采取的反制措施。
《规定》第14、15条明确了反制措施在执行过程中的定期评估及调整机制。通过明确救济途径,提高了受制裁主体对其行为后果的预见性,激励其改正并消除影响。受制裁主体可通过采取“减损措施”申请解除对其境内财产采取的查扣冻措施、恢复进出口,恢复境内投资资格等,有效降低在中国市场遭受长期损失的风险。
5
不执行反制措施的例外规定
(《规定》第16条)
《规定》没有对反制措施的执行“一刀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受制裁主体的相对方继续与其进行交易等活动的灵活性。相对方通过向有关部门说明理由,在取得“同意”后可继续进行原活动。《规定》未明确有权申请“同意”的主体,但结合《反外国制裁法》第6条第(3)项(“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指受制裁主体,编者注)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及第11条(“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能够申请免于执行反制措施的主体应为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
《规定》第16条为保护境内主体的合法权益保留了空间,避免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格局中因交易对手被采取反制措施而误伤。
6
不执行反制措施的后果
(《规定》第13条)
《规定》第13条赋予有权机关对不执行反制措施的主体:
责令改正;
禁止或限制其:
-
从事政府采购、招标投标以及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活动;
-
从境外接收或者向境外提供数据、个人信息;
-
出境、在我国境内停留居留等。
结合《反外国制裁法》第6条第(3)项及第11条,《规定》第13条中的禁止和限制措施应仅适用于我国境内未依法执行反制措施的组织和个人,而不包括境外主体。为满足该条所提出的合规要求,外贸活动频繁的境内企业,应尽早制定制裁风险工作指引,建立交易对手制裁风险筛查机制,反制措施执行机制等,避免因疏忽大意而被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甚至被迫终止货物、技术等进出口活动,遭受重大商业损失。
7
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后果
(《规定》第17、18条)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因此,《规定》第17、18条的适用对象为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境外的组织和个人)。
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对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进行约谈,责令改正,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规定》第17条未对“相应处理措施”的具体形式予以明确。但可预见的是,我国有权机关对采取“处理措施”享有广泛的裁量权。以外国金融机构为例,如其执行或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其境内主体的主管机关(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能依据《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该机构的境内主体采取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经营许可证等措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直接责任人员亦可能被给予纪律处分。
《规定》第18条重申了合法权益因“歧视性限制措施”遭受侵害的我国公民、组织有权向我国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侵害主体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2025年3月初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及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一案。该案中,我国某公司与外国某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后因外国公司受第三国制裁影响中止履行合同义务,我国法院首次适用《反外国制裁法》受理诉讼并促成和解,使我国公司顺利获得8400余万元建造款。此案系首起当事人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提起的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南京海事法院通过释明中国法下协助执行外国单边制裁的法律后果,在39天内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充分彰显了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法律威慑力。
如中国企业的合同相对方因执行“限制性歧视措施”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中国企业可援引本条规定在中国法院起诉,从而掌握化解纠纷的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对因“危害行为”遭受损失的境内主体,本条未明确赋予其提起侵权之诉的诉权,对该部分主体的具体救济途径仍待明确,笔者将持续关注。
此外,《规定》第18条可能对外国判决、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执行产生影响。为支持“限制性歧视措施”而作出的外国判决、裁决,可能因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而面临被不予承认和执行的风险。
8
强力应对外国国家、组织、个人
的滥诉行为(《规定》第19条)
2020年疫情期间,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在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中国提起多起“集团诉讼”,要求中国赔偿因新冠疫情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此外,密苏里州在密苏里联邦法院起诉要求中方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对外国政府、实体等通过诉讼手段进行的“甩锅行为”,《规定》第19条将予以强力反击。
如相关诉讼被认定为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推动、实施、参与诉讼和判决执行的外国国家、组织或个人及“相关的组织或个人”均可能被列入反制清单,成为反制措施的对象。“相关的组织和个人”的范围虽未予明确,但其外延可能非常广泛,包括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个人的配偶、直系亲属等(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第3点)。
本条应引起为境外诉讼程序提供法律服务、调查服务、送达服务机构的高度重视。律师事务所及案件承办律师如代表外方当事人参与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诉讼程序,将面临被列入反制清单、被采取反制措施的风险。
本条彰显了我国对境外主体滥诉行为的强力应对,为督促相关行为人“三思而后行”提供了保障。
9
鼓励服务机构在反外国制裁领域
发挥专业优势(《规定》第20条)
《规定》第20条充分肯定了专业服务机构在推动反外国制裁方面的作用,并鼓励其为境内主体有效执行反制措施提供服务。以律师行业为例:律师可协助外贸企业建立交易对手制裁风险筛查机制、制裁风险评估机制、反制措施执行机制等,以协助出海企业关注业务运行中的制裁风险,依法执行反制措施。律师也可以向被采取反制措施的外国主体提供反制名单移除等服务,为其采取改正、消除影响等措施提供支持。此外,律师在代理因“限制性歧视措施”涉诉案件的过程中可积累相关经验,在实务中检验并完善我国对单边制裁的应对之道。
结语
《规定》的出台,为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有效应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提供了重要法律工具,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贡献了中国方案。欲善其事,先利其器。随着中国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作用不断突显,通过完善反制措施、细化程序、强化执行,中国将打出精准反制的组合拳,为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简介
方建伟 律师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业务领域:合规和调查,诉讼仲裁,反垄断和竞争法
杨芮 律师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业务领域:诉讼仲裁、合规和调查、制裁
本文转自跨境争议与监督法律观察公众号,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