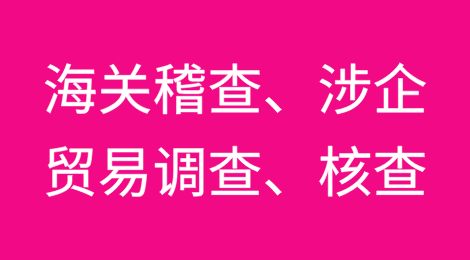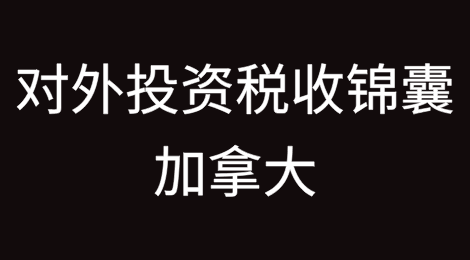俄罗斯企业不再惧怕制裁:背景与深层原因解析

俄罗斯企业不再惧怕制裁:背景与深层原因解析。(根据The Bell等网站资讯整理,仅供参考)

近年来,俄罗斯企业对西方制裁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将 “西方制裁” 视为主要商业风险的俄罗斯企业高管比例,已从 2022 年俄乌冲突初期的 63% 降至 2024 年的 42%,2025 年进一步下滑至 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8% 的高管将劳动短缺列为首要挑战,42% 则担忧高融资成本。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俄罗斯企业在长期制裁压力下适应与转型的结果,背后交织着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支撑与心理认知转变等多重因素。
一、背景:从 “突发冲击” 到 “常态环境” 的制裁演进
俄罗斯企业对制裁的 “脱敏”,源于长达十余年的制裁常态化进程。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西方制裁便开始逐步施加于俄罗斯经济,涉及能源、金融、军工等关键领域。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 2022 年 —— 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实施了史上最严厉的极限制裁:切断部分银行与 SWIFT 系统的连接、冻结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面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 短期内,俄罗斯经济遭遇剧烈震荡:外汇市场暴跌、进口渠道中断、支付系统瘫痪,企业普遍将制裁视为 “生存级威胁”。
然而,经过三年的调整,制裁已从 “突发危机” 转化为 “背景噪音”。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制裁的范围、力度与实施方式逐渐固化,不再具备 2022 年时的 “突袭性”。对俄罗斯企业而言,制裁从 “不可预测的黑天鹅” 变成了 “可预期的常量”,这为其系统性适应提供了时间窗口。
二、制裁常态化:企业完成结构性适应与替代机制建设
制裁威胁弱化的首要原因,是俄罗斯企业已建立起应对制裁的成熟体系,实现了从 “被动承受” 到 “主动适应” 的转变。
制裁成为 “已知风险”,企业完成全链条调整
自 2014 年首次遭遇制裁以来,俄罗斯企业便开启了 “抗制裁” 准备。2022 年极限制裁后,这种调整进入加速期:
在财务层面,企业普遍减少外币依赖,增加卢布资产配置,通过国有银行规避国际结算风险;
在供应链层面,重构采购网络,将关键设备、原材料的来源从欧美转向非西方国家;
在市场层面,主动收缩对西方市场的依赖,转而开拓 “友好国家” 业务。如今,这种调整已内化为企业运营的 “默认设置”,制裁带来的边际冲击持续减弱。
替代路径全面成型,打破西方封锁
为突破西方在金融、供应链与市场领域的封锁,俄罗斯构建了多层次替代体系:
•金融支付替代:俄罗斯版 SWIFT 系统(SPFS)用户数量持续扩大,与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建立本币清算机制,MIR 支付卡在 “友好国家” 普及率提升,有效规避了美元、欧元结算限制;
•供应链重组:关键设备与原材料采购重心转向中国、印度、中亚等地区,例如汽车产业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占比从 2022 年的 15% 升至 2025 年的 48%,能源设备采购中 “非西方供应商” 份额突破 60%;
•市场版图重构:面向 “友好国家” 的出口占比从 2022 年的 38% 增至 2025 年的 62%,化肥、能源等行业甚至因西方退出而获得更大市场空间 —— 俄罗斯天然气对中印出口量较 2022 年增长近一倍,化肥出口额三年间增长 45%。
三、国家强力介入:“战时经济” 模式下的企业支撑体系
在制裁压力下,俄罗斯政府通过 “战时经济” 策略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支撑,成为缓解外部冲击的关键力量。
财政与国有资本的 “兜底” 作用
依托油气收入回升(2024 年俄罗斯油气出口收入较 2022 年增长 23%),政府将财政资源向关键领域倾斜:对军工、基建、农业等行业提供直接补贴,仅 2024 年军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助就达 GDP 的 3.2%;国有银行通过政策性贷款为大型企业提供 “流动性安全垫”,2023-2024 年国有银行发放的企业纾困贷款超过 5 万亿卢布,使信用违约风险较 2022 年下降 60%。同时,资本管制政策有效遏制了资金外流,稳定了卢布汇率,为企业经营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
战争需求催生新增长极
冲突带来的 “战时需求” 意外为部分行业注入活力。武器制造、军事物流、建筑(军工设施与受损地区重建)等行业订单激增,2024 年俄罗斯军工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0%;农业、食品加工等 “自给自足” 型产业因进口替代政策获得扩张空间,粮食出口量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IT 服务行业则因西方企业退出,本土市场份额从 2022 年的 35% 升至 2025 年的 78%。这种结构性增长让企业意识到,制裁背景下仍有生存与发展的机遇。
四、焦点转移:内部结构性问题取代制裁成核心担忧
当制裁的冲击逐渐可控,俄罗斯企业的目光开始转向更棘手的内部挑战。这些 “内生瓶颈” 已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障碍。
劳动力短缺与融资困境凸显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态势尤为突出:一方面,人口自然减员与战争导致的适龄劳动人口流失叠加,2024 年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较 2022 年减少 120 万;另一方面,移民流入因地缘局势下降 30%,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建筑业的用工荒。48% 的企业表示,“招不到合适员工” 已影响生产计划。
融资成本高企同样困扰企业:为稳定汇率与抑制通胀,俄罗斯央行长期维持高利率(2025 年基准率仍达 12%),叠加信贷风险溢价上升,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较 2022 年前上涨近一倍。42% 的企业认为,“高利息压力” 已超过制裁对现金流的影响。
长期结构性隐患待解
除短期压力外,技术老化、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人口结构恶化等长期问题更令企业担忧。由于西方高科技产品进口受限,俄罗斯制造业设备更新周期从制裁前的 8 年延长至 15 年,汽车、电子等行业技术代差扩大;国内消费因通胀与收入增长乏力持续疲软,2024 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仅恢复至 2021 年的 92%;而人口老龄化加剧(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18%),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对企业而言,这些 “内部消耗” 比可预期的制裁更难应对。
五、心理韧性:从 “恐慌” 到 “适应” 的认知转变
企业对制裁态度的软化,还源于心理层面的深刻变化。2022 年制裁初期的 “至暗时刻”—— 外汇市场崩溃、银行挤兑、物流中断 —— 让企业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如今,幸存者普遍形成 “抗压体质”,认为 “最坏情况已过,再严厉的制裁也能找到对策”。
同时,“爱国经济” 叙事强化了企业的心理支撑。政府与媒体将制裁塑造为 “西方遏制俄罗斯崛起的工具”,鼓励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实现 “经济主权”。这种叙事下,许多企业负责人公开表示,“制裁倒逼我们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反而增强了独立性”。
结语
俄罗斯企业对制裁的 “恐惧消散”,并非因为制裁失去效力,而是其性质已从 “致命威胁” 转化为 “可管理的常态化风险”。长达十余年的制裁压力,推动俄罗斯在替代机制建设、国家资源调配与企业适应性上实现了系统性升级。但与此同时,劳动短缺、融资高企等内部问题的凸显,也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之路,将更多取决于能否解决 “内功” 短板 —— 这或许比应对外部制裁更具挑战性。
本文原载于“信保民工”微信公众号,如有转载或复制请联系“信保民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